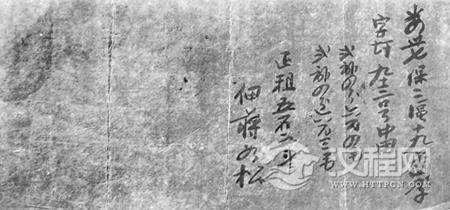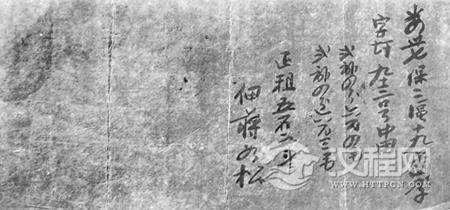
清朝名贴
名片在现代社会颇为通行,但名片并不是现代才有东西,这种时髦的东西也不是舶来品,名片在中国有着很长的历史。名片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汉代,在西汉时,名片是用竹木做的,称作“谒”。所以,中国还应算使用名片最早的国家。
名片古时称它为“名刺”或“谒”,到了明清时期又称“名帖”,一直沿用到1949年前,之后就称“名片”了。它像文书的发展一样,最初也是使用竹、木简,以后逐渐改用纸。
汉代名刺已很流行,刺上一般要写明姓名爵里,故又称“爵里刺”。汉刘熙《释名》中解释说爵里刺就是“刺书其官爵及郡县乡里也”。至于下级或晚辈谒见上级或长辈,也可称谒,如果同时送礼,则还要加书所送钱物的数量。这令人想起《史记